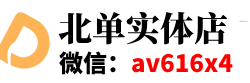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会上去踢两脚,有时候连长、指导员也会上场助兴,真有点“人人皆球星”的味道。
周鑫 摄
喜欢上足球,还是缘于在军营里的那段时光。
来部队之前,真不知足球为何物。上学时,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学校的孩子,能有两个篮球大家胡乱抢抢就不错了,这个黑白相间的“尤物”,几乎都没见过。新兵连的生活开始,周日的操场上,不时会看到一些老兵们踢球的身影,我总是远远地望着,有老兵也招呼我加入,我虽然有些胆怯,但渐渐地与足球的距离在拉近。
下连队了,连队是个傍山而建的营房,整体面积显得狭小。营房是一面靠着山体,其他三面相围的构造,看上去是一个“北京四合院”的形状,中间又被分割成两半:前院,是连队早晨出操站队的地方,后院,则是每日吃饭排队之处。就后院这块不足50平米的院心,是战友们饭前踢上几脚足球的“小球场”。其实,连队也有一块篮球场可当小足球场用,只是因为它建在连队院子外面,所以大伙偷懒,就选择在饭堂前“操练”了。
1990年夏天,下连队不久,因为工作需要我被抽调到机关宣传科报道组工作。报道组一共四个人,两官两兵。其中一位姓于的干事是江西九江人,地道的球迷。于干事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还没找对象,星期天,他总会组织机关里的一帮年轻的干部、战士踢球。因为他有一脚右脚任意球打门的绝活,所以大伙给他起了个雅号“于右任”。

准确地说,我的“球迷”生涯,就是从这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的。当年的世界杯开幕式,在于干事的强拉硬拽下,深夜时分我与他一起坐在了电视机前。那一届世界杯虽然看得津津有味,但也着实有些稀里糊涂,谁是冠军,谁是“副班长”,谁是“金靴”,谁是“大佬”,我并不太了解和关心,我记住的只是男人的阳刚之气与精湛的足球技艺在这项激情碰撞的运动中得到的完美体现。
回到老连队才发现,连里的球迷还真不少,“院子足球场”已成为战友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位青岛和淄博的战友成为主力军,我们经常一起在院子里或篮球场两处“切磋”,慢慢地,我的“球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连队机务室的技师老祝是东北人,也是一名“业余足球裁判”,他敦实的身板、红红的脸膛,说起话来低沉有力,平时我们在院子或篮球场踢“五人制”足球时,他经常做“场外指导”。每当我们嫌小场踢得不过瘾,和山下兄弟连队的战士相约到大的专业球场“决战”时,老祝就换上裁判服,成了我们两队的“中间人”了。每次开踢前,他总会给我们双方讲一些场上的注意事项,以及避免犯规的“技巧”,每每此刻,我们总会被他“刺激”得有一种“大敌当前,舍我其谁”的斗志与豪情。
那几年,只要没有工作任务,我们经常会组织十二三个人,在篮球场上踢足球。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会上去踢两脚,有时候连长、指导员也会上场助兴,真有点“人人皆球星”的味道。要说球场上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也不少。为了规则的见解不同而争执,甚至横眉冷对;至于说顶着隆隆雷声、冒着倾盆大雨,在外面“持续作战”的事更是举不胜举。有一次踢球时,湖南籍战友小尹由于速度过于猛烈,收不住脚,竟然撞到了篮球场外的一棵树干上,当时眉骨开裂,面部血流如注。到山坡下的卫生队一番包扎后,这位小老弟可一点都没闲着,依旧上场充当“组织中卫”,直到尽兴而归。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真正喜欢上了足球这项体育运动,不仅仅是喜欢它的激情,它的难以预测和意外惊喜,更多的是那种同心协力、不畏艰难、勇敢前进的团队合作精神吧。退伍后,曾一度身处上海这个大都市,总会隔三岔五去现场看球。再后来就是在电视、网络里经常有欧美的各种联赛直播,但不管球队多有名,也无论比赛多么激动人心,与军营生活中结下的这份深厚足球情缘相比,一切精彩,又似乎黯然失色了许多。
难忘军营生活,难忘军营足球。
(袁卫东/文)
北单在那里买请加店主微信:av616X4